12、终了
上期节目我们说到:
1093年,宋哲宗亲政“绍圣绍述”,他要彻底继承神宗的变法路线,以章惇为首的新党人物被悉数启用。新党上台之后,竭尽全力的打击报复“元祐党人”。罢黜、监禁、贬谪的圣旨密如雨下。
第二年苏轼被贬惠州,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”。15年之后,又重新回到了当年被贬黄州的境遇,失去了所有的权利。3年之后,他又被贬到了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”的蛮荒之地海南孤岛。
这让苏轼重新回归到那个我们喜爱的苏东坡,在苦难中一次次的完成超越,一次次的完成自我拯救。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更重要的是,他以超然旷达的出世精神,成就了孤忠为民的入世事业。
想尽一切办法,尽可能的帮助身边的人。“无病而多蓄药,不饮而多酿酒”“劳己以为人”。教人们开荒种地,讲学明道,帮这蛮荒之地文明开化。
一个人想要真正的摆脱孤独与苦难,就需要和人在一起,把自己的命运与周围的人捆绑在一起,才能完成超越。
在苏东坡最后几年的人生时光里,他始终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古人“兼济天下”的品行与操守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1100年正月,年仅23岁的宋哲宗突然驾崩,没有留下子嗣。在神宗妻子向太后的主持下,哲总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,是为徽宗。
这时,国家组织已烂,元气已衰。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范纯仁等等那一代仁宗皇帝留下的德才兼备的儒臣早已尽数凋零。而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,也因遭受迫害而不复当年为理想从政的壮志雄心。
徽宗继位之后,向太后摄政了一段时间,尽管她在半年之后就还政于子,但直到第二年的元月去世之前,他都始终在保护着元祐诸臣,被贬岭海之间的元祐党人,一律赦免,或予升迁,或至少恢复了人身自由。
向太后就和他的婆婆高太后一样,能明辨是非,知人善任,在这一点上远胜过她的儿子。能言善辩的吕慧卿,精明能干的蔡京,在向太后眼中都被归入了“坏人”之列,只可惜这位英明的太后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弟弟苏辙获赦之后,立刻北上,一路跑到了东京旁边的颍昌待着,就位待命,随时准备接受朝廷的任用。
而哥哥苏轼则完全不一样,他接到诏命之后磨磨蹭蹭,六月份才慢慢悠悠的开始往北走,一路上游山玩水,访故会友。
6月20日这天晚上,他动身离开了居住3年的海南,横渡琼州海峡,在船上他写下了那首被世代身处逆境的人反复吟诵的七律:
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其中借用了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一则典故:司马道子夜半闲坐,赞叹天空晴朗,皓月皎洁,没有半点云彩,旁边人说:我觉得有点淡淡的云彩点缀反而更美。司马道子开玩笑说:“你自己心里脏,就不要把天空也弄脏了。”
苏轼借用这个典故,暗骂了那些栽赃陷害自己的人。如今这些栽赃污名就像被风卷走的云,而自己的心就像这天空与大海,澄澈无垠,未曾改变。
对于屡次贬谪,苏轼内心没有丝毫悔意,不以为耻反以为荣,无怨无悔,把这当成是平生最激荡胸怀的游历。
当时舆论公认,苏氏兄弟作为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旧党领袖,一定会得到朝廷的重用。章惇的儿子章援还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,当时章惇已经被贬,章援在信中委婉的表示,希望苏轼如果有机会,能够救助自己的父亲,或者至少不要打击报复。
苏轼在回信中,非但没有将自己年老投荒的苦难归罪于章惇,反而还以“海康风土不甚恶,寒热皆适中,船舶到时,四方物多有”来宽慰章援,胸襟气度,超乎常人。
从“建中靖国”到“崇宁”
其实苏轼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。
徽宗即位第二年,将年号改为“建中靖国”,意思是:我既不偏向新党,也不偏向旧党,而是在二者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,我要安定国家,结束党争。
但是“建中靖国”并不是之前的“元祐更化”,是在新旧两党人兼收并蓄的同时,两党中的极端份子也要被压制。“新党”中风头最劲的蔡京、蔡卞兄弟被放离京城,而苏氏兄弟作为“旧党”领袖,也在不被重用之列。
“左不可用轼、辙,右不可用京、卞”是决策核心的共识,“建中靖国”的局面就是以蔡氏兄弟和苏氏兄弟同时出局为代价。
这或许就是苏轼不急于北归的原因,也解释了苏辙为何急行北上之后,也只能停留在颍昌,而不能更进一步。
“建中靖国”的年号仅仅只用了一年,第二年便改元“崇宁”,意思是以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政治方针作为崇尚的对象,“新党”卷土重来。
因《水浒传》被我们熟知的蔡京权倾天下,大宋的宰相之位终于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小人。
蔡京为了把政敌一网打尽,赶尽杀绝,将309人列为“奸党”,然后把这份黑名单刻在了石碑上,并要求在全国各县立碑。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、苏辙等等一众元祐大臣的名字全都在石碑之上,这些人及其后代永世不得为官,这便是著名的“元祐党人碑”。
而苏东坡自己不用再经受这些磨难了,或许对他来说,也是一种幸运吧。
“勉强,那就错了”
1101年6月,东坡在常州病倒了,身体每况愈下。到7月18日的时候,他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便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:“我平生未尝为恶,自信不会进地狱,你们不用担心。”他交代让弟弟子由给自己写墓志铭,不回四川湄洲老家了,就把自己跟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上。
到了7月28日,东坡在弥留之际,老友维琳方丈在他耳边说:“现在,要想来生啊!”东坡轻声回应:“西天或许有,空想前往,又有何用呢?”“你还是要做如是想啊!”东坡留下了最后一句话:“勉强想,那就错了。”
东坡是对的。世间万事,理应顺其自然,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每时每刻对世界,对人生不经意的了悟当中,绝非是这一时一刻之下,穷尽全力所能抵达。
以东坡对佛学的体悟和对生活的态度而言,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。即便真有西方极乐,对于东坡而言,那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,对生活每一刻的真实把握之中。对此,他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与自信。
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,东坡一言未发,溘然长逝,享年64岁,面对死亡,他平静而安详。
一生光明磊落,无怨无悔,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,对人生的了然洞察,消解了病痛之苦与死亡之惧。
一个月之前,东坡在金山寺,即兴写下一首诗,表达了当时的心情,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:
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
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
对于仕途,苏轼也许早已心如槁木死灰、了无渴望,但也正因如此,他的身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,思想也如不系之舟,进入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。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经历,对苏轼自幼渴望兴邦治国的功业理想而言,具有反讽意味;但如果就贬居三地时他所获得的文学成就,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而言,谁又能说不是一桩巨大的人生功业呢?
如果没有这一段挫折的磨练,也就不可能有后人心目中的那个苏东坡了。
人格标杆
东坡的一生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:他为后世万代树立了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。
无论遇到多大的磨难,始终不曾放弃对家国百姓的责任。无论自己的境遇如何,面对怎样的威权压迫,始终敢于仗义执言。这绝不是鲁莽冒进的个人主义,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可贵人格。
在苏东坡的身上,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,有杜甫执着坚守的忠义魂,有白居易穷达通融的从容风度,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情怀。东坡的思想与人格,既是先贤传承而来的结晶,也是对这一切传统的融汇与开拓。
他在追求人生解脱的时候,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,否则他的文字不会那么的一往情深;他在追求人生完满的时候,不止于人伦亲情,否则他的文章不会如此旷达超逸。他是那么的丰厚、充实、平静、温和,饱含人间深情与超越智慧。
可以说,苏东坡就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,完善,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。
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,这个伟大的文学天才,这个黎民百姓的亲密朋友,他将勤政爱民的执着精神,超然物外的达观气质,天真炙热的盎然情趣,从容优雅的潇洒风采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,成就了一个可爱、伟大与不朽的灵魂,永远都将在中国文化的星河中川流不息、熠熠生辉。
作为苏东坡的爱慕者,能与你分享他的故事我非常的荣幸。感谢这个世界有他来过,让我们在这个喧嚣慌乱的时代,依然能感受到一丝爽朗的清风。
好了,关于苏东坡,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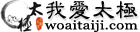 我爱太极
我爱太极